作者被骗被拒绝之后,便“想饮一些酒”,好“让灵魂失重”。但显然灵魂是不存在的,所以作者的饮酒并不能让灵魂失重,也就不能排遣心中的忧愁和痛苦,不能排遣心中的求得解脱的梦想。作者这时的内心是痛苦的,因为“一想到终将是你的路人,便觉得,沦为整个世界的路人”。这时,连风也似乎和自己过不去了,“风虽大,都绕过我灵魂”便表达了一种解脱无望,内心痛苦的感觉。
最后说一下这句话的特点。前半句风虽大包含着让风来带走痛苦的希望,因为作者本身不能排遣,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外力来帮他解脱,帮他豁达。
后半句都绕过我灵魂,将灵魂具体化,象征着作者的痛苦和难以排遣的愁绪。风已经很大了,但还是绕过了,说明忧愁之巨,连风都无法撼动。
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
——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在写《 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这篇文章时,我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生”与“死”是一个东西,大脑的思想是“过去”的延续,如果大脑每天都在思考“过去”与“未来”的话永远不可能接受新东西。
如果死亡意味着思考的结束,那么我们便可以做到此刻死亡,每分钟都在死,每一秒都在死;让大脑里的想法死去,因为它们只是“过去”的延续;让关于“未来”的想法死去,因为它们还没有到来,让它们死去。
我们从来不害怕未知,我们只是一直在害怕失去已知,失去现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死亡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既然未知的事物不可揣摩,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害怕?
当时因为考虑到文章的结构所以没有继续叙述下去。这段时间沉淀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要将这一点叙述完整。也借此展开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
当你真正做到每时每秒都在“死亡”,让大脑里的一切想法全部立即死去,那么你才能够真正地做到“活在当下”。如果你对自己说要“活在当下”却没能做到“死亡”,那么“活在当下”就成为了一种逃避的手段。你只是现在不去想,但它们还存在。 记忆是一个封存在时间里的箱子,它会在你毫无防备之时突然打开,让你措手不及。
“爱”与“爱情”是两个概念,但它们之间的界限其实非常模糊。《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如是说道: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一种宁静而又充实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上的另一个状态就是文字无法表达的一个状态了;但“爱情”是能被文字勾勒出图像的,虽然也不可能被描述清楚,但它是可以被讨论的。 所以现在,让我们回归主题。
01
“爱情的本质在于爱的对象并非实物,它仅存于情人的想象之中。”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下的这句话完全可以当作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注脚。爱玛十三岁时进入了修道院附设的寄宿女校念书,她在那里接受着贵族式的教育。她倾心于教堂的花卉、宗教的音乐,并在浪漫主义小说的熏陶下成长。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想象力会特别丰富。而沉醉于虚无缥缈的幻想便是爱玛的童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 小说的时间背景是19世纪40年代,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确立的时期。 此时法国的资产阶级也在“七月革命”后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且,伴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渐推进,法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工农业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摄影作品《资本主义的最高产物(在约翰·哈特菲尔德生活)》,作者乔·斯彭斯,后现代艺术流派作品。)
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对人的精神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爱玛梦想着过小竹房子的生活,想象着有一位好心的小哥哥,情意缠绵,爬上比钟楼还要高的大树去摘红果子,或者赤着脚在沙滩上跑,给她抱来一个鸟巢;她沉浸在罗曼蒂克的幻想中。她是一个典型的消极浪漫主义者,她渴望着一种“传奇”式的爱情。
在与查理结婚之前,爱情对她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只存在于诗歌中的灿烂幻想。当她真的结婚以后,她发现了这不是她想要的爱情。但是她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她一股脑地把这些错误归根在自己的丈夫身上。因为他 “谈吐像人行道一样平板,见解庸俗,如同来往行人一般衣著寻常,激不起情绪,也激不起笑或者梦想。”
(画作《爱情万岁》,作者妮基·桑法勒,超现实主义流派作品。)
爱想象中的人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可当他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爱他们就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同样是追求“想象中的爱情”,在纪德的《窄门》中,杰罗姆把阿莉莎放在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他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追逐者,一个想要往上爬到与阿莉莎一高度的追逐者。杰罗姆单凭自身的想象把阿莉莎抬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这种想象是具象化的。
但爱玛不同,她追求的是一个形式化的生活。 在这种“生活“里面她只要拥有爱情的凄美、用金钱粉饰出来的“浪漫”便足矣,至于具体的对象是谁对她来说根本无所谓。所以当她窥见她对其并不了解的“上流 社会 ”的生活时,她眼前的生活枯竭了,因为查理完全不符合爱玛想象中的那种形象。
在爱玛的心目中,她的丈夫应该是一位骑士,精通马术,会制造浪漫,并且能随时随地地吟诵出美妙的诗歌。但查理医生可不是这样子的。查理与爱玛完全是相反的两个人,他先后结过两次婚,但是他在两次婚姻中都是“毫无地位可言”,这一段婚姻也不例外。 查理对待工作勤勤恳恳,对待妻子也尽量满足;为了爱玛的 健康 问题,他们举家迁居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在金钱方面,查理不仅从来没有对爱玛的奢侈消费有丝毫的不满与反对,反而竭尽全力地去满足她。 但是,在精神层面,查理对妻子的心灵世界是一无所知的,更不用说满足妻子对浪漫爱情的需求了。所以,爱玛的出轨和抑郁而终可以说是必然的事。
(画作《骑士》,作者乔治·德·基里科,新巴洛克风格流派作品)
自然主义文学的特点在于作家不在叙述故事中添加如何自己的主观评论,作家只是故事的叙述者,除此之外便销声匿迹。而作为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福楼拜将这一点运用得淋漓尽致。他完全消失在了叙述后面,做了一个冷漠的解剖学者。如果说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是对骑士小说的清算,那么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就是对消极浪漫主义这一文学派别的清算。
02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史的光谱上,爱玛这个形象与堂吉诃德是十分相近的。他(她)们都是阅读了太多的书,以至于自己受蛊惑而深陷其中的人; 桑塔格将这种心理症候称之为嗜读症。对他们来说,贫瘠的现实生活无法承载他们对于生活的想象,以至于他们宁愿相信书中的生活是更“真实”的生活,而眼前这“普通的”现实生活在它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画作《死之岛》,作者阿诺德·勃克林,象征主义流派作品。)
堂吉诃德沉溺于骑士小说,便妄图将骑士的事迹践行于现实中;爱玛则是因受了浪漫言情小说的蛊惑,开始不顾现实地追求罗曼蒂克的爱情。她不愿意接受事实,她把自己隐藏在想象力的背后,把自己关在了自己所设的牢笼之中。 人是一个热衷于“比较”的动物。人是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当一个人处在一个在“比较”的状态之时,他是没有“满足”可言的。
狄德罗在 《关于美的根源及其本质的哲学探讨》中提出了“美的分类”:
“美”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事物,这种客观事物的“美”是受许多因素影响的,因而它并不是非常重要。
而真正重要的是主观事物的“美”,它又细分为两种,一种是“真实的美”,即事物本身。或者换句话说,它是所有人看见了都会觉得美的事物。另一种是“见到的美”,这一种“美”是通过比较而产生的美。是通过与另一个事物相对比而产生的美。
(哲学家德尼·狄德罗)
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所有人都觉得美”的情况是非常少的, 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见到的美”,通过贬低一个事物从而拔高另一个事物的“美”。
所以,依据这一点,狄德罗随后又提出了 “美在关系” 这一概念。就是要看与“美”的事物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中,它针对的对象又是谁。只有在一个特定的关系之中时,“美”才能够被凸显出来。
爱玛所追求的是一种浪漫而又凄楚的爱情。她想要拥有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美好爱情。但包法利医生(也就是查理)和爱玛之间缺乏心灵上的沟通,他们两个人一个是现实的,另一个则是幻想的。 在查理的身上爱玛感受不到激情,查理不能满足爱玛的美好幻想,所以她无法接受他的平庸,转而继续寻找着她的内心的“特定对象”。
(画作《暴风雨中的皮拉摩斯和提斯柏》,作者尼古拉·普桑,古典主义流派作品。)
要明确的一点是,爱玛虽然憧憬于上流 社会 的生活,但是她的憧憬并不是出于对另一个阶层生活的羡慕,而是因为她见识到那些上流 社会 的舞会之后,发现这些片段恰好合于她在书中所看到的某些情景。 借助这些名贵的首饰以及华丽的衣裳,她对于生活的热情和想象一下子被释放了出来,她认为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她心目中的“真实”而又充满“意义”的生活。
让我们顺着狄德罗的观点继续往下走。
爱玛的“爱情”所针对的对象并不是查理。但并不是一开始她就察觉到了这一点。在刚结婚时,爱玛试图在丈夫身上去塑造这种理想中的美好,但是均以失败告终。当内心无法被填满时,她只能转向外部生活,希冀找到能为她提供这些片段式的想象的男人成为她的寄托。 对方可能是个无赖、是个伪君子;但是对爱玛来说,只要对方提供了片刻合于她想象中的爱情的话语以及场景,她就会把对方想象成一个完美的模样。她随时等待着一个符合她想象的片段,一旦想象得到了满足,她便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献祭出去。
这种热情可以为平淡的生活增添色彩,但也可以对生活造成毁灭。
爱玛死了。但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
03
还是狄德罗。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狄德罗效应”:
18世纪法国有个哲学家叫丹尼斯·狄德罗。有一天,朋友送他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睡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可他穿着华贵的睡袍在书房走来走去时,总觉得家具不是破旧不堪,就是风格不对,地毯的针脚也粗得吓人。于是,为了与睡袍配套,旧的东西先后更新,书房终于跟上了睡袍的档次,可他却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自己居然被一件睡袍胁迫了",就把这种感觉写成一篇文章叫《与旧睡袍别离之后的烦恼》。
200年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朱丽叶·施罗尔在《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狄德罗效应",专指人们在拥有了一件新的物品后,不断配置与其相适应的物品,以达到心理上平衡的现象。
在今天看来,“狄德罗”效应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消费主义的陷阱” 。用简单的话来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是你在定义事物,而是事物在定义你。而人就是这样被物化的。
人也是一个“两栖动物”。他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同时他又生活在“符号世界”里。现实世界就是感官的世界,是你眼前的世界。而符号世界由心理活动以及思考而构成的世界。 两者没有孰轻孰重,一个人麻木到不会思考与沉醉在虚无中是一样的不可取。
但是对于爱玛来说,符号世界已经覆盖了现实世界,前者在她看来远比于后者更有意义。 符号世界是很容易被外界所建构的, 爱玛便是如此,这已经不是她在定义“爱情”,而是“爱情”在定义她。她深受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那些对于爱情的观念已经深入了她的内心之中成为了执念。当她追求不到自己“想象中的爱恋”之时,她便从外部世界寻找一个寄托,妄想通过这片刻的欢愉填满她空虚的内心。
(画作《灯塔》,作者查尔斯·拉皮克,野兽派作品。)
爱玛的悲剧在于 她把偶尔当作了经常,把偶然当作了必然 。书上那些凄美的爱情故事,写男主与女主相互爱慕最终出逃或者殉情等等; 这些故事之所以经典且被人广为传颂,原因正是因为这些事发生的概率极低。所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会广为流传;所以“自挂东南枝”那种坚贞不渝的爱情至今被人赞颂。
爱玛不明白, 所以从一开始,她追求的就是“想象中的爱恋”。
她想要得到的不是“自己的爱情”而是“别人的爱情”。 她的爱情观是被别人设计好的。 不是她在定义爱情,而是爱情在定义她。她的“自我”不是自己所寻找的,而是被外界所建构的。
那你呢?你的自我是自己找到的,还是外界帮你建构的?
你的爱情生活是自己的,还是你在想方设法的要过上与“别人的爱情”相同的爱情生活?
究竟是你在定义世界,还是世界在定义你?
本文来自作者[焦建辉]投稿,不代表伍月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uyuewh.cn/yue/240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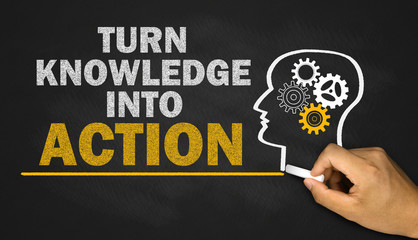





评论列表(3条)
我是伍月号的签约作者“焦建辉”
本文概览:作者被骗被拒绝之后,便“想饮一些酒”,好“让灵魂失重”。但显然灵魂是不存在的,所以作者的饮酒并不能让灵魂失重,也就不能排遣心中的忧愁和痛苦,不能排遣心中的求得解脱的梦想。作者这...
文章不错《怎么理解西贝的“风虽大 都绕过我灵魂”》内容很有帮助